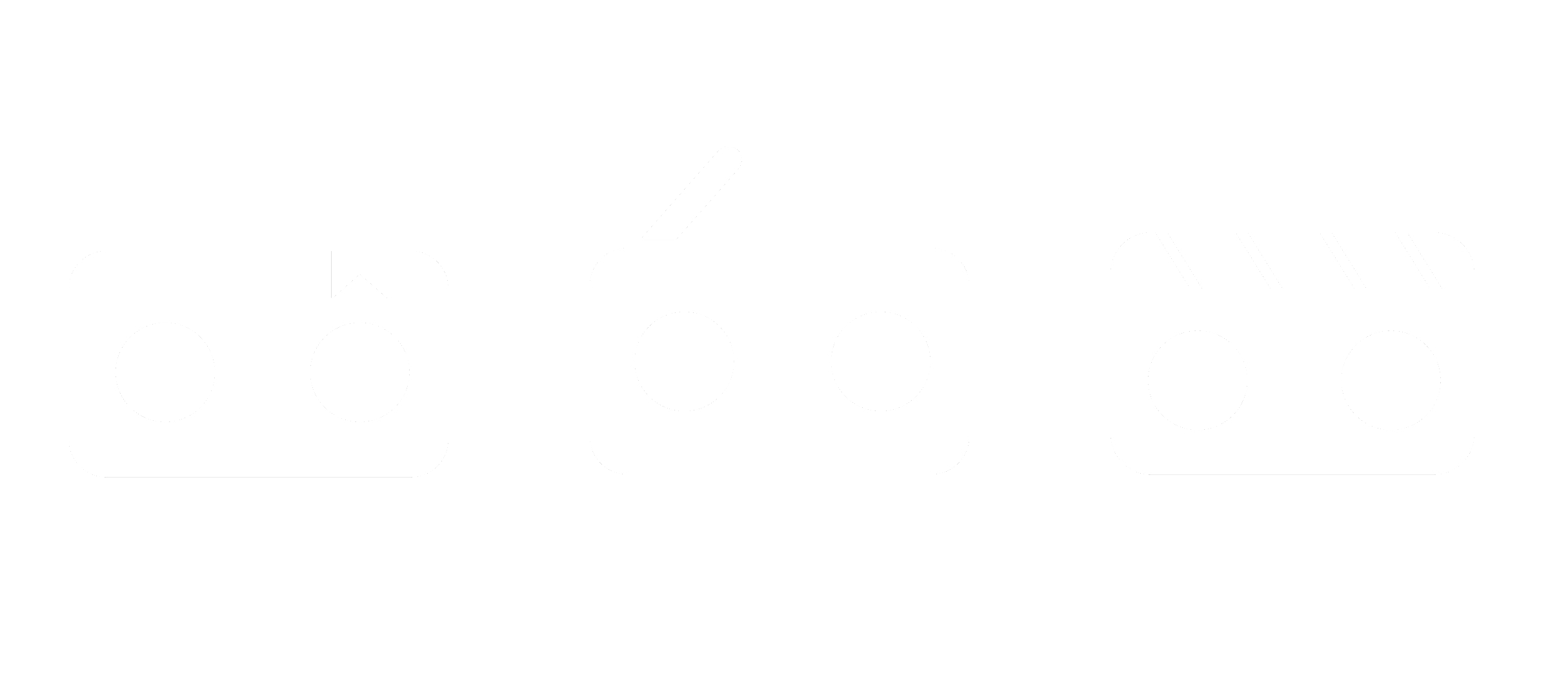埃及公路札记 (更新中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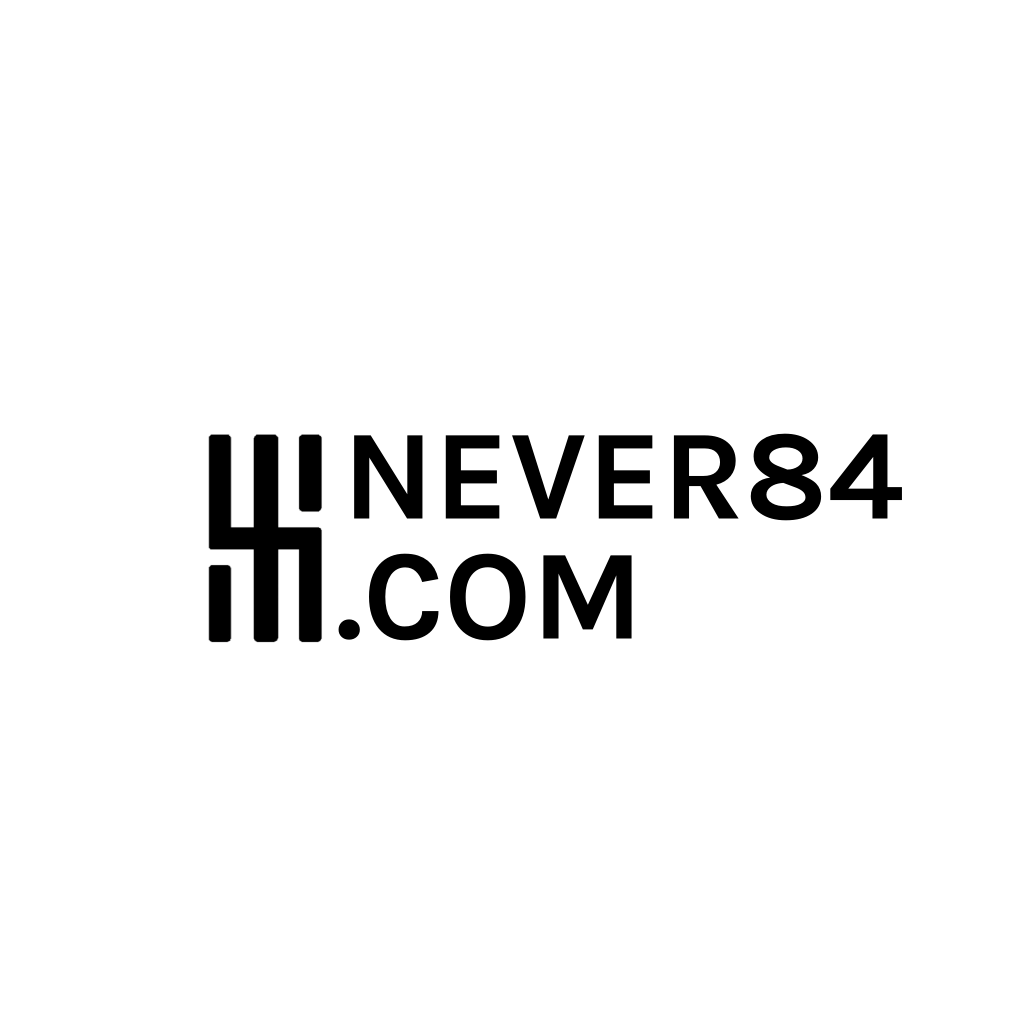
引言
开罗的交通是一场没有规则的 Disco,方向盘的每次转动都在与混乱共舞;
亚历山大的咖啡馆是时间的避难所,每一杯浓郁的土耳其咖啡里都沉淀着地中海的晨昏与旧梦;
清晨的卡纳克神庙,阳光斜切过列柱厅的千年石柱,在斑驳的象形文字上投下神谕般的阴影;
阿布辛贝的日出,将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染成琥珀色,仿佛众神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;
而红海的傍晚,满月从海平面升起,月光如金色的绸缎铺展在波浪与沙漠上。
街道上不时传来清真寺悠扬的宣礼声,头巾紧裹的虔诚妇人匆匆掠过西餐厅的橱窗;
高档餐厅里,本土啤酒 Sakara 在玻璃杯中泛起泡沫。
孩子们的眼神有时天真无邪,扑上来抱着你说“I love you”;
有时又带着事故般的狡黠,拍着的车窗叫着“Money, Money”。
高速收费站的收费员找不开零钱,摆摆手示意你直接通过;
而另一条路上,收费员则攥着少找的 20 埃镑,冲你诡谲一笑:“Welcome to Egypt”。
埃及的一切,都在撕裂与缝合中生长,像神庙裂缝中倔强绽放的野花。
有时候,你恨不得立刻逃离;
但更多时候,在亚历山大的海边公路,在卢克索星空倾斜的夜晚小道,在金字塔下被车辙碾出的尘土路面...
你会忽然感叹道 —— 你怎能不爱这个世界。

初遇开罗,混乱中启程
从成都起飞的川航航班即将降落开罗,天际刚泛起一层薄金,舷窗外突然提携三个几何形的阴影。在赭色沙漠的晨雾里,三座金字塔如同被遗忘的坐标,沉默地切割着地平线。丁达尔效应为它们勾勒出朦胧的光边,像古埃及文明发出的微弱信号。空乘开始播报落地时间,机舱里充满了人们的惊叹和手机相机快门声。掠过金字塔,飞机落地;四千年的光阴,没有延误地抵达。

飞机落地后立刻开始办理入境手续。完成落地签、过边检、取行李,随后行李慌慌张张地通过安检。整个过程还算顺利,开罗机场给我的第一印象不差,基础设施比预想中完善。
在Orange柜台买了电话卡,资费不贵,埃及国家代码是+20,手机号码以01开头。候机厅休息区稍作整顿,用洗手间时发现埃及厕所整体挺干净,甚至带着好闻的香薰味道。经过11小时飞行居然不觉得累,可能还处于兴奋状态。
Sixt租车柜台前都是中国的“勇士”。排前面的海南小哥遇到了麻烦,他本来预定的日产阳光没车了,车行给他临时升级车型,但要求两天后归还升级车辆。由于他行程时间和我相同,这个方案显然不合适。见他英语沟通不算顺畅,我主动帮忙与工作人员协商,随后车行同意全程免费升级,前提是给个好评。最终他拿到辆配置不错的吉利SUV。后面排队的是一家三口,行程只有8天。大家熟悉后,我提议建个微信群互相照应,海南小哥主动建了群,这个群后来在旅途中帮了大忙。
轮到我办理时,真切感受到埃及人的办事效率——倒不觉得是缺点,整个社会氛围确实没那么内卷。工作人员慢悠悠办完手续,让我去航站楼出口等车。
拖着两个行李箱和三个背包走出航站楼,第一次零距离接触埃及。虽然是晴天,天空泛着昏黄。高架桥上车辆川流不息,司机们开车风格狂野,满街都是老旧车型。航站楼外三三两两的埃及人边抽烟边说笑,对我们这些外国人见怪不怪。但即便在现代化机场外,对我来说,空气里依然弥漫着异国情调。
终于等到那辆斯巴鲁XV,这是一辆全时四驱的SUV。车很酷,但车身布满刮痕——尽管里程数才六万多公里。我倒吸凉气,仔细用手机环拍车身视频留存。送车的是个憨厚的埃及中年男子,英语不好但态度友善。他坐后排帮我们把车开出机场,下车后,真正的自驾游就此开始。
在机场附近找空地停车调整:重新设定座椅,安置好行李,熟悉车辆功能。意外发现这车居然带Carplay,之前准备的手机支架和蓝牙FM发射器都白买了,算是意外之喜。我们特地把 osmo pocket 固定在仪表台中央,用作行车记录仪,以备不时之需。后来这个行为只坚持了两天,因为发现根本没有必要。

短暂休整后正式出发。今天要直接从开罗机场开往亚历山大,这座地中海海滨城市位于尼罗河三角洲西侧,全程180公里,预计行驶两个半小时。
踩下油门,车辆驶入开罗街道时,一切都充满新鲜感。起初车流稀疏,驾驶节奏还算从容。刚开不久竟遇见租车时结识的海南小哥,双方鸣笛示意后分道扬镳。这份始于机场的缘分持续了整个旅程,成为珍贵的记忆。
进入市区后,传说中「地狱级」的驾驶难度开始显现。这里没有真正的交通规则,行人、突突车与各类车辆时刻在进行动态博弈。斑马线或许曾经存在过,如今早已被磨蚀殆尽。横穿马路的人们带着理直气壮的敏捷与从容,司机必须时刻预判他们的行进路线。满载的微型巴士和突突车堪称道路霸主,它们以毫米级的车距表演着街头特技,在拥堵中游刃有余。谷歌地图在这里频繁失灵,某个复杂路口让我循环三圈不得其解,最终放弃导航自行探路反而成功突围。
开罗的第一印象如下组图,路况复杂的时候家属有些紧张没有拍。





但所有这些混乱,竟让我催生出某种难以名状的感动。当我注视着窗外破败建筑间穿梭的人群,眼眶时常莫名发热——或许因为不时出现微笑示意我先行的人们,或许因为在衰败中依然蓬勃的生命力,又或许单纯源于对全然陌生文明模式的震撼。这种感动在后续行程中反复涌现。
穿行在埃及的街巷时,常产生身处平行时空的错觉。我虽然常往返于中欧之间,却是首次如此真切地触摸到「第三世界」的脉动。在主流叙事被西方主导的当今世界,这个阿拉伯古国仍保持着自成体系的生存智慧。这让我想到,这世界不知有多少被主流语境忽视的古老文明,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生不息。
亚历山大,晴
从开罗到亚历山大的路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好开,后来我才发现是因为在开罗市区时走错了路。一路上换了几条公路,经过了不少城镇,但比起开罗市区的驾驶,这段路已经算轻松了。
离开开罗后,我们在一个加油站停了车,不是为了加油,而是想用之前在机场换的埃镑买点东西。商店里的工作人员很友好,我们买了两杯咖啡和一些面包,用了现金。这是我们在埃及的第一次购物。虽然大多数店员不懂英文,但通过比划,他们都能明白我们的意思。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,但从他们的眼神里,我能感受到他们对我们的友好。
接下来的路程还算顺利。我们第一次遇到警察查岗,但他们似乎对游客不太在意,直接放行了。不过,快到亚历山大酒店时,高德导航带我们走的路被封住了。路卡的工作人员穿着邋遢,说话含糊不清,还试图拿我的手机。经过一番无效沟通,我意识到他想要钱。我给了他10埃镑,他示意不够,要20埃镑。我爽快地答应了,他也爽快地移开了路障。来埃及之前,我就对这种情况有所准备,20埃镑也就相当于三块钱人民币。不过,让我意外的是,这种情况在之后的旅程中并不常见。
我们预定的酒店叫Rixos,是雅高旗下的度假酒店,位于亚历山大东侧的Montaza宫。选择这里是因为我早就听说亚历山大的市区交通混乱,不敢贸然开车进去。但没想到,第一天我还是陷入了亚历山大的车流中。快到酒店时,我才发现Montaza景区外是一个客流集散中心,小巴在拥挤的道路上随意停靠、穿梭。
在埃及,本地人似乎很少坐大巴,城市之间的交通被小型巴士(类似国内的货拉拉)垄断。我不清楚背后的原因,但这些小巴的生意很好,车里总是挤满了乘客。车里的埃及人似乎已经习惯了小巴的拥挤和司机的鲁莽,淡定地看着窗外。偶尔我们向他们招手,他们也会笑着回应。这些小巴司机技术了得,总能精确计算与周围车辆的最小安全距离,真是“万花丛中过,片叶不沾身”。
费了好大劲,我终于把车折腾进了Montaza宫。景区的安保人员核实了我们的预订后,我们顺利进入。Montaza宫又称埃及夏宫,是埃及末代皇帝法鲁克的夏季行宫。法鲁克荒淫无道,他的宫殿自然极尽奢华。现在的Montaza宫是一个巨大的景区,里面有椰枣树林和精心打理的花园,干净整洁,临近海滩。与景区外的混乱相比,这里简直是世外桃源。
景区的工作人员帮我们停好车,我们顺利办理了入住。Rixos是当地政府开发Montaza景区的一部分,是新建的旅游度假项目之一。房间比我想象中好很多,阳台正对着整洁的海滩,远处是蓝色的地中海,远处的Montaza灯塔点缀着海平面,景色宜人。

飞行11小时,又在异国开了200公里车,入住后却并不觉得累。我们简单洗漱后,便在景区里逛了逛。作为一个封闭景区,埃及本地人也需要买票进入Montaza宫。景区里人很多,正值当地学校假期,孩子们特别多。值得一提的是,孩子们大多由戴头巾的妇女照看,看得出当地妇女的工作率可能不高。
Montaza景区内干净舒适,我们走到Montaza桥时,有个小女孩一直偷偷看我们。我们假装没注意,继续往前走,后来她鼓起勇气走到我家属面前说:“I love you。” 这异国他乡突如其来的善意让人感动。家属拥抱了她,接着又来了很多埃及孩子,一一与我们拥抱。我拍拍他们的背,说:“I love you too。” 然后我们合影,不舍地道别,真是世界大同的感觉。
我们沿着海岸线走了一段,穿过映着椰枣树影的大理石路面和修剪整齐的花园,我们出了Montaza宫景区。离开景区大门的瞬间,仿佛跨进了另一个世界:破败的路面上挤满破旧的老爷车,永不停歇的喇叭声像背景噪音般持续轰鸣,空气里飘着刺鼻的汽车尾气味,街道旁的高楼外墙上尽是斑驳的裂痕。我对家属说:”这才是真实的埃及。”

我们叫了一辆 Uber,这是我这次旅程中唯一一次没有选择 Uber Comfort(即“专车”)的行程。埃及的车牌采用阿拉伯文字,而非我们熟悉的“阿拉伯数字”(冷知识:“阿拉伯数字”其实并非源自阿拉伯)。来接我们的是一辆雪佛兰小车,我反复确认车牌上的阿拉伯文字,确保没有上错车。车辆外观破旧不堪,车内更是污渍斑斑,自此之后,我再也没敢尝试最低档的 Uber(即“快车”)。从酒店打车到亚历山大市中心,总共才一百三十多埃镑,价格倒是不贵。
前往市中心的路沿着地中海海滨公路蜿蜒而行,乘坐 Uber 让我可以安心地欣赏窗外的风景。正值傍晚,阳光穿透云层洒在波光粼粼的地中海上,海边的围栏旁,三三两两的人们悠闲地坐着休憩。远处的天际线紧凑、陈旧却充满烟火气。这就是千年古城亚历山大,美丽、深邃。
亚历山大的咖啡馆很有名,在阿拉伯世界,酒精被限制,咖啡馆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社交场所,取代了酒吧的角色。我家属挑选了一家百年老店——Delices。我和她各点了一杯土耳其咖啡,我的加奶,她的原味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喝土耳其咖啡,彻底被震撼了。这种味道是我们从没体验过的,与快餐式的意式咖啡截然不同。它让我想起小时候我爸第一次泡功夫茶给我喝的那种感觉——醇厚、讲究、耐人寻味。土耳其咖啡非常浓郁,细密的咖啡渣悬浮在杯中,显然是经过精心烹制,而非机器冲泡的千篇一律。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蛋糕,我们随意挑了几块,味道倒是平平无奇,但那两杯咖啡,颠覆了我的认知。

在接下来的旅程中,我和家属每天都会喝上至少一杯土耳其咖啡。我常常想,在星巴克席卷全球之前,咖啡本该是土耳其人围坐铜壶旁,慢火细煮的社交仪式。当工业化生产将“咖啡”简化成按键即出的黑色液体,那些需要等待与沉淀的本真味道,是否正如亚历山大那些褪色的老建筑一般,悄然消逝在所谓“主流”的阴影里?
在 Delices 喝完咖啡后,我们换了一家餐厅吃饭。这是一家西餐厅,橱窗干净,门口冷冷清清。我有些犹豫,不确定它是否营业,推开门进去后才发现,里面别有洞天。服务员穿着白衬衣、红马甲,打着领结,礼貌得体地迎上来,把我们引到二楼一个僻静的座位。餐厅里客人不多,每张桌子都铺着整洁的桌布,几桌食客安静地用着刀叉进餐。置身其中,让人恍惚间以为到了欧洲——这种刻意营造的优雅反而让我不自在。
这里供应红酒,我自然地点了一杯埃及本土红酒,以至于后来我误以为埃及的餐厅都可以点酒(实际上只有高级餐厅才提供)。我和家属点了牛排和沙拉,味道很一般,但服务还算周到。只是,这家餐厅的氛围和外面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仿佛两个极端。不过,在这安静的环境里,我和家属进行了一次深聊,也算是意外的收获。

走出餐厅,夜晚的亚历山大突然活了过来。这里的夜晚真热闹,街道上摩肩擦踵,有很多衣着时尚的女性,自在地逛着街,看来这里的治安不会差。街道两边的商店零次栉比,路面上的车辆也似乎比白天更加拥挤。夜晚的亚历山大真美,充满了市井烟火气。
在这里,商店老板往往习惯一个人坐在店门口,看着来往行人,也不玩手机。夜幕下,他们的剪影仿佛是沉思者,静静地与喧嚣的城市共存。这里的数字化程度显然比国内落后,很多生意仍然依靠传统的面对面交易。但这似乎也不是一件坏事,正是这样的方式,让街头更热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