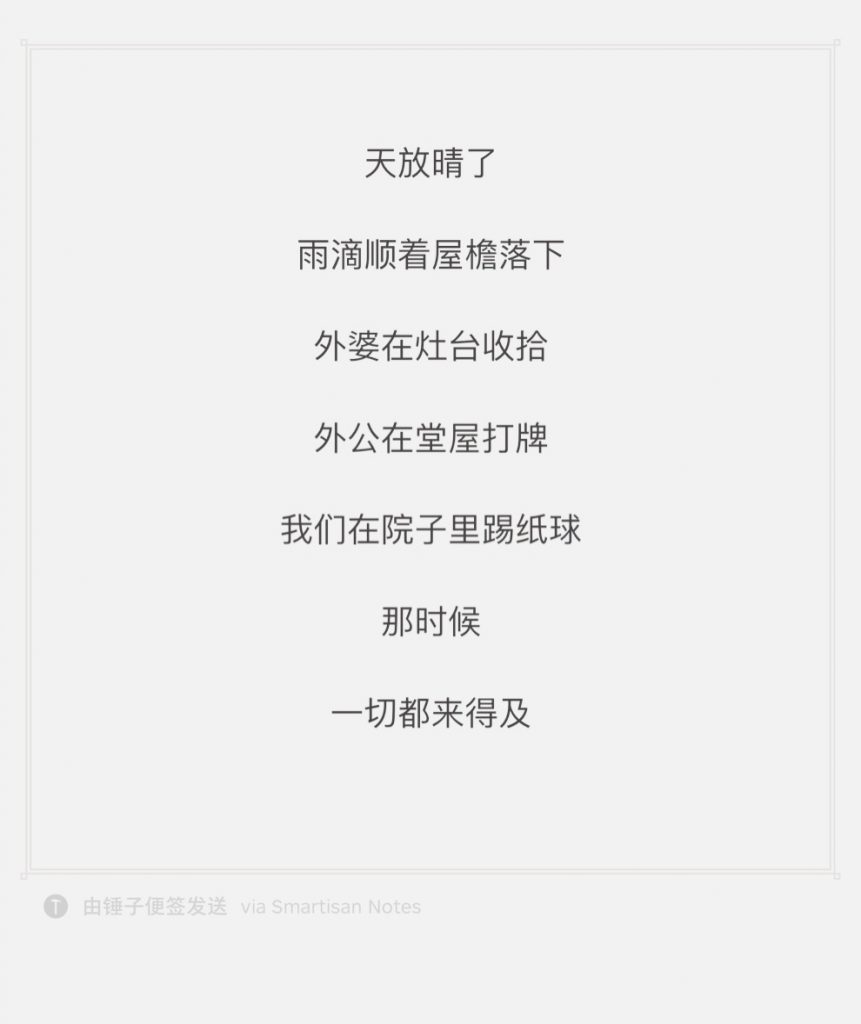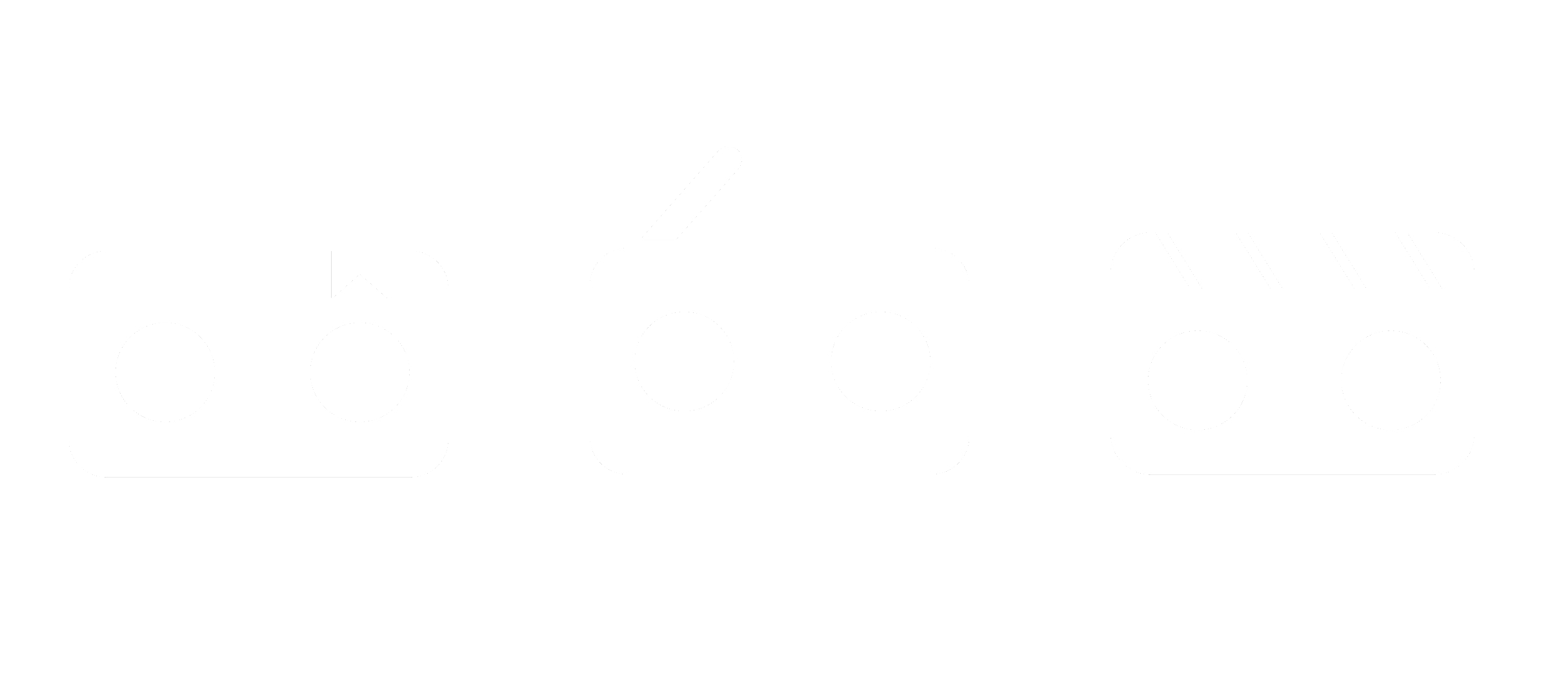外婆
To the ones who had to depart, see you down the road.
赵婷,《无依之地》

外婆走了。
想来关于外婆我其实知道的并不多。我甚至记不清她的名字,也很少有人提过她的名字。似乎对于普通人,老了,名字也就不那么重要了。
记忆中关于外婆最多的画面是,老太太端坐在火炉子旁,边用火钳翻弄炉子里的秸秆,边慈祥地若有所思地发呆。炉子里的火光把老太太脸上的褶子照得分外深刻,猜不出她到底在想着什么。
每年的暑假,几个孩子都会去乡下外婆家的老院子里呆上几天,这几乎是我对童年最美好的记忆。
在乡下,孩子们终于有了伙伴和自由,小院子里踢纸球,里屋时不时传来外婆爽朗的笑声。院子内种着两颗银杏树,一株玫瑰花,地面总是被外婆收拾地干干净净。
孩子们都爱吃外婆的红烧肉。外公会骑着自行车去后面的镇子上买些肉,交给外婆做红烧肉给我们吃。外婆做的红烧肉甜甜的,肥瘦相间,糯而不柴。
外婆从不让孩子们靠近河边,她说湖里有“水獭木”,会拉小孩子下河。每当我们生了些小毛病,外婆会在碗里放些水,然后尝试将筷子竖立在碗中。如果能筷子能立起来,就代表是不干净的东西上了身,外婆会去买些纸烧一烧,请脏东西走。
外婆从来不缺鬼故事,她笃信鬼神的存在。想到死去的大姨,外婆总是会哭。眼泪从她被褶皱包围的眼睛里流出,顺着苍老的脸颊落下。但我知道,外婆不惧怕死亡,她和外公早早地把棺木打好了放在堂屋里。
孩子们一下子就长大了些,回乡次数越来越少。每次回乡还是能吃上红烧肉。不知是在外好吃的吃多了,还是外婆手艺下降了,红烧肉渐渐没那么香了。孩子们还是会夸赞外婆,更多是出于捧场,很难说是发自内心。
仿佛外面的世界变大了,外婆家的院子变小了。
直到孩子们再大了些,看到行将就木的外公外婆,和同样一天天老去的自己,才领悟到,有一种“人间值得”是:外婆在做饭,外公在打牌,我们在院子里踢着球。
小时候总是被外婆讲的鬼故事吓到,但长大了反而会被这些鬼故事安慰到。电影《过昭关》里,孙子怕鬼,爷爷对孙子说:“变成鬼还是好事哩,爷爷想见到的人,就都能见到了。”
前两周,我回家看外婆。外婆已如风中之烛,不能动也少有意识了。但她还是能认出我,一遍遍地叫着我。 外婆一直都叫孩子们“宝宝”,甚至也这么叫我的妈妈,但此时的外婆才更像是一个在襁褓中的孩子。我不忍又心疼,只能一遍遍地摸着外婆的头,说,没事的外婆。
时间的齿轮只会往前运作,人要思旧不念旧。我相信,我和外婆会再相见。在那时,她也会轻拂我的额头,说,没事的。
写到这,我特地向家人问了外婆的名字。我的外婆,她叫谷炳凤。